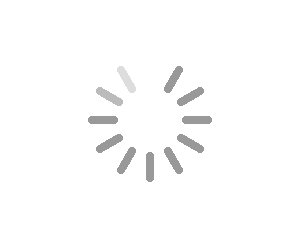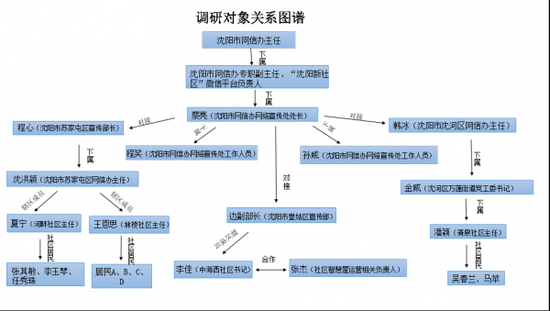来源时间为:2022-03-10
是知名媒体人伊险峰和杨樱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一经出版,便得到了陈嘉映、梁文道、罗新、严飞、李海鹏、班宇等诸多学者作家的高度评价。
书的主角,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伊险峰的初中同学,他们如今都是口碑甚佳的专业人士,也都出生于工人家庭。他们所在的1970年代生人,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他们生活的城市沈阳,在这个过程中处境复杂——从计划经济工业重镇到一个落伍者,有强大的失落感。
两位主人公的人生,说被规划也好,或者借着模糊的目标去努力也好,总的来说,就是逃离他们原来家庭所在的阶级的过程,我们现在叫做“阶层跃升”。
这本书讲述的是有关个人成长的故事。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两位医生以“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如何努力适应社会,努力成为“社会人”的过程。
以下为作家、媒体人李海鹏为本书所撰写的序言。
-----------
文/李海鹏
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有一种典型叙事,就是人物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被称为“成熟”的精神腐败过程。
本书所写的两位医生的故事,倘若严厉地说,大致就是这样。他们的“成熟”始于人生发轫时期与社会潜规则碰撞导致的心理创伤,止于一种悲剧性与喜剧性参半的尴尬状态,也就是既不能忠实于自己的真实心意,与“社会”保持距离,又掌握不了适度地沆瀣一气的复杂技巧。这种故事,每到社会变革时期就会流行,在变革意愿低落时期又会沉寂。在兴起和沉寂的循环往复中,其中一个搞笑又颇具意义的问题——“我们都这么庸俗了,怎么还是不快乐?”,始终不曾得到答案,因而变得恼人。
如今,就连这一问题背后的“人文精神”也被视为无意义之物,问题也就不必解答了。
这本书的特别价值,在于以这两位医生的半生经历为线索,呈现了沈阳过去四十年令人叹息和沉默的民间社会史;更在于作者以知识人的认真态度和故事人的写作能力,描摹了上述问题的核心答案,即促使人们精神腐败的社会因素。
书中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编织出一只捕兽笼,试图捕捉人们口耳相传的神秘的“社会”,令人一睹其真容,又以社会学式的耐心,具体而微地再现了“社会”塑造、摧折和屈服人们的步骤。
▍隔膜于真实社会的“奖学金男孩”
在20世纪80年代,沈阳还处在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好光景”之时,书中的两位医生都是父母较为偏爱、着力培养的孩子,他们被要求戒除一种“随弯就弯”的放任倾向,远离遍布四周的恶习。他们被持续地置于成为好孩子的压力之下,正如作者意识到的,其本质是被要求摒除自身的工人阶级习性。日后两位医生功成名就,正得益于他们良好地回应了上述要求。
当他们的家庭在国企下岗潮中面临困境之时,教育仍作为优先事项被坚持下来。他们的弱点就此埋下了伏笔——他们是“奖学金男孩”,隔膜于真实的社会。比如他们都被要求诚实,待到成年之后,不得不补习必要而复杂的说谎艺术,却为时已晚。
结果直到四十多岁,两位医生仍不得不时常懊恼于自己的不够“社会”。
同时,城市的失败也导致父亲们的失败——本书第十章就此有着敏锐而精彩的刻画——母亲们因此成为家庭中更有用处也更具能量的一方。
两位母亲,一位以身段灵活见长,一位以勤奋自律为荣,都具备现实的野心和势利的远见,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两位医生的人格。两位父亲的形象则要脆弱和模糊得多,或因循本分,或沉迷阅读,显然没能称职地完成“何为男子汉”的言传身教。考虑到在沈阳,争夺啄食顺位是一份终生事业,夸耀男子气概是一项基本技能,父亲们缺乏影响这一事实显然深有影响。
在书中,罗伯特·E.帕克的一条理论显得尤为刺目: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
两位医生的原生家庭跨越三十年的奋斗在事实上始终紧紧围绕这句话,在这场奋斗中调动的能量、毅力、耐心、机谋是如此之多,堪比战争所需,然而这部平民史诗的主题只是“不要成为废弃物”而已。
他们成功了,恰如书中对张晓刚父母的终生成就的概括:
“在整个社会崩塌、解体、堕落的过程中,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充沛的精力、智慧和爱,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跟了上来,不但没有掉队,而且逆势上升。他们带三个孩子实现了阶层跃迁,进入到富裕而且专业的群体之中,与90年代那个迷茫困顿、看不到出路的沈阳截然不同。”
但他们从中感受到的幸福、欣慰,还不如庆幸多,又不得不伴随着疲惫和怀疑。
▍推崇男性气概的“社会”
在沈阳,人们口耳相传的“社会”正如书中所说,“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准确的外延和内涵的词”,一方面是具体语境中的民间用语,灵活性多过规范性,另一方面,词义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不过约略而言,这一“社会”也就是缺少透明度的社会,是无数人际联盟同时作用下的一种过分复杂的游戏规则。
比如在书中,张医生和王医生跟无数沈阳人一样,受到一种显而易见的文化蒙蔽,相当推崇男性气概。对于“理想的男人应该勇敢、仗义和慷慨”这一神话的深信不疑,几乎可以成为沈阳定义的一部分。然而事实上,沈阳“社会”对男人的真实要求更类似于微型军阀,在意政治技巧多过在意男性气概,不带有政治技巧的男性气概则是一种累赘甚至致命的习性。
“朋友”,才是那个能在无数沈阳人的心灵中激起神奇能量的词,在隐藏其后的裸猿体系中,联盟则是能量的来源。
拥有政治技巧的人拥有联盟的支持,拥有政治资源的人则领导联盟。联盟可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尤其是利润丰厚的暗地里的交易,联盟也对外竖起壁垒。“打通”多个联盟的能力因而至关重要,而男性气概,尽管令人目眩神迷,却只是涂抹在这一社会结构上的神话外壳而已。这样的社会结构自然会催生一种“腐败就是全部问题所在”的世界观,以及一种“把自身的失败全部归因于没能跻身于腐败圈层”的人生观。
其结果是,无数个联盟的总和,也就是“社会”,成了无处不在的流动之物,遍布城市的每一寸空间。哪怕是在廉价的酒馆里,乃至亲族聚会的温馨场景中,也免不了要上演一出出既慷慨真诚,又表里不一的权力的游戏。
在自由经济发展的好年景,现代文明规则会扫荡类似的“社会”体系,但是由于坏年景时时归来,微型军阀们负隅顽抗,固守了地盘,这样的事情在第三世界普遍发生。沈阳正是这一辽阔图景中的一个小点。正如书中两位医生注意到的,相比中国“南方”地区,沈阳更守旧,更顽固,更为高昂的社会成本所拖累。
在这一图景中,两位医生想更“社会”化也力有不逮。
他们接受的教育,对于习得民间政治技巧毫无帮助。正如书中所说,掌握这种政治技巧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经验和资源。要掌握它们可能首先需要家庭的传承,而平民家庭多半对此不甚了了。在其他条件接近的情况下,这种经验和资源将是决定社会地位的核心因素。他们作为“奖学金男孩”毕业之后,如常言所道,“遭受社会的毒打”,也就不足为奇。
因此书中记录,王平医生多次说,“要是会来事儿的话,这个东西就解决了”。“会来事儿”乃是表露乖巧和体贴的“妾妇之道”,是一种基本的政治技巧,其要点恰恰在于违背男性气概,因而他拒绝掌握。张晓刚医生也曾在紧要关头,徘徊在某个联盟之外而行贿无门。在整本书中,他们都极少提到“朋友”或其同义词,他们谋求成功的路径是跟医院同事共同“创业”或进军网络医疗平台,并不拥有能量十足的“社会”联盟。
发生在两位医生身上的最戏剧化的情节,是戏剧化情节的不曾发生,即两位医生都不谴责这一令他们难受的“社会”。
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确不是批评者,与其他工人阶级子弟相比,他们的优势之一正是不批评,或者说不叛逆。在少年时期,他们是什么样的少年,取决于被父母要求成为什么样的少年;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中年男人,也取决于被“社会”要求成为什么样的中年男人。
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和身边的人都缺少基本的人文常识和相应的判断力。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沈阳这座城市忽视“谴责”与“抱怨”的差别,而“抱怨”会被认为是缺乏男性气概的表现。在回顾面对“社会”的多次挫败之时,两位医生都以一种男子汉的气度,把一切归咎于自己。
对于父亲的失败,他们也简单地归结为能力匮乏,不愿思考国企改制转型期间,“社会”对成年男性的伤害。他们似乎默默地信守着一句格言:挨打要立正。
最终,两位医生都成了不情不愿的荷花式的人物,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却染不上。他们的社会身份走向中产阶级专业人才的舞台,精神世界却留在工人阶级的童年小屋里。
▍沈阳人的精神世界
如今他们是优秀的医生,有责任感和医德。他们能辨善恶,保留着某种程度的独立人格,拒绝下作,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经营自己,又不钻营。同时,他们思考却缺乏思维工具,因此常常表现为思考流于表面而且过分自信。他们是不假思索的男权主义者。他们鄙视文科,鄙视政工干部,又轻易地将二者混为一谈。他们鄙视太“社会”而成功的人,也鄙视“社会”的失败者,比如不懂得利用威胁手段而轻易诉诸武力的同事。出于草率的心态,他们尊重得少,蔑视得多。
大致上,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相对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们有着犬儒的精神世界。他们是博士,却沾染了当地的“红脖子”色彩。在这一系列特征中甚少自觉的成分,多半是男性自尊和某种可称为“沈阳性”的精神特质的曲折表达。
问题的核心正在于,他们是地域性的人物。像无数出生在沈阳的人一样,他们被染上了强烈的沈阳色彩。在持续终生的社会化过程中被沈阳的“社会”塑造、摧折并向其屈服,正是两位医生为何如此又如何至此的原因。
本书的第一作者,伊险峰,中国媒体界凤毛麟角的人物,也出生于沈阳,而且是书中两位主角的初中同学。他也许是单纯地看中了沈阳这座城市的戏剧性和深度,也可能是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熟悉的世界,因而选择了本书的题材。无论如何,在这一题材上,两位作者完成了一份杰出、精彩而重要的工作。在描摹沈阳特色的“社会”和显微呈现沈阳人的精神世界的方面,他们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能用两位医生的视角目睹沈阳几十年来的社会景观的话,我们会更理解他们。我们会看到,在他们四十多年的生活经验中,在他们祖父两辈的言传身教中,在他们的专业阅读范围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在沈阳,“社会”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会看到,过去三十年间,沈阳完成了从人到建筑、景观和城市记忆的去工业化的过程,一切天翻地覆,“社会”却近乎永恒。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理解,对于两位医生来说,是否喜欢“社会”就不再重要,它的对错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承认并尊重它的存在。这就是他们的“楚门的世界”。每一个地域性的人物都比其他人更多地受到社会布景的摆布,他们也是如此。
沈阳人的精神世界,如书中呈现的,无论是犬儒的、男子气概的、波希米亚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究其根本,也是尊严、价值和情感的表现,其情可悯。
这一精神世界几乎有着瑰丽的一面,却又只是水面上颤抖的波纹,映照出的是历史的伤害,以及“社会”这条龙带来的恐惧的影子。
▼
《张医生与王医生》
伊险峰杨樱著
东北,非虚构,写作,社会
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